最近一个月,详细了解了一下国产Android MID(平板电脑),打算年底入手一台,毕竟现在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。ARM微处理器有很多阵营方案,并广泛应用于手机、MID设备,当前主流的是A10核心方案。
国产品牌众多,就七寸而言,比较可以的有艾诺7、台电p76ti、纽曼M7等,感谢Imp3论坛,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。 继续阅读
引子
2001年9月13日,多云间小雨,农历七月廿六。
晨曦初现,初秋乍冷,我的惺忪很快被村里的大喇叭驱散,早间新闻播报:全国的党员同志们在热烈地学习三个代表,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被飞机撞塌了,但是原因扑朔迷离—-这些消息固然关乎宏旨,但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嵩山山脉脚下的小山村,显然没有人关注和探讨,大家都在忙活着地里的庄稼。于我而言,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,那就是启程去郑州,上学报到,开始新的生活。
家里一片忙碌,妈一早就起来收拾,为爸和我装点行李。我们带了被褥,还有三千块钱学费(但是并不够当年四千多的学费)——为了保证绝对安全,这笔巨款被缝在妈了我贴身的口袋了。另外,我还带了几本书,包括一本1970年代出版的关于青年成长的励志书,和一本盗版的《中国新诗鉴赏辞典》。
拖拉机突突的冒着黑烟在路上颠簸,我扶着装着鼓囊行李的化肥编织袋,路边是我熟悉的田野,鸟儿停在电线上探着脑袋,不时的叽叽喳喳,像是道别,让我的心里更充满了忐忑。要到陌生和繁华的地方,这对于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村男孩来说,多少是一个挑战,要知道,十几年里,我大部分时间的生活半径不超过十五公里。为了适应“大城市”的生活,妈建议我留个偏分的发型——但是很遗憾,因为短发蓄的时间比较短,这看起来非常滑稽,另外我也不习惯穿皮鞋,脚哏得慌。
话说回来,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——这是大部分中学老师的评价,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兴奋和期待,毕竟这是一个告别黄土背朝天、汗流浃背老子,然后做个体面的“公家人”(城里人)的机会。
彼时交通并不发达,我们先坐拖拉机,一路颠簸到乡上,然后搭到破烂的小巴到登封县城,再坐闷热的中巴,经新密,到郑州。
进城! 继续阅读
继续阅读

Simon最近打电话,说父亲的文稿想印刷出来,请我帮忙制作一个可打印的PDF版本。于是我想到了Adobe Indesign,虽然之前没用过,但是毕竟是相通的,于是边学边练,快速制作了出来,印刷之后效果还不错,呵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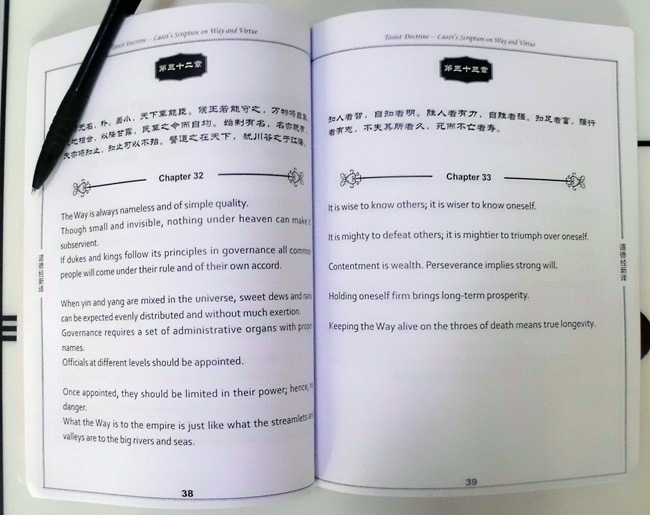
每天骑车,匆匆上下班,路过铁路桥,看到花坛里的姹紫嫣红,花开花落,人各忙碌。在这个繁忙的城市,除了清洁工,有谁会停下来感悟下春天的气息呢?
摘李商隐《落花》自勉:
高阁客竟去,小园花乱飞。
参差连曲陌,迢递送斜晖。
肠断未忍扫,眼穿仍欲稀。
芳心向春尽,所得是沾衣。
不知不觉中,来上海已经三年了。在别人的一篇文章里,我被描述成“隐居在这个超级繁忙的东方大都市”。我自己呢,很矛盾,出于农人的习性,并没有太强的节奏感,通信基本靠吼,时间基本靠估。但是在城市的磨砺和工作的要求,又让我不得不努力加严谨的规划、使用时间。这把我搞得很光鲜也很狼狈,就像《摩登时代》里无所适从的卓别林。
走在初秋的上海街头,微风拂面。我想,空气,跟时间差不多吧,前者流动的时候,是风;而后者流动的时候,是一个人的成长和蜕变,一群人的变革和历史。 继续阅读